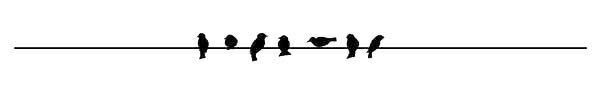小哼哼诞生记
夕同学的预产期是2015年9月29日。不过,预产期只是依据Naegele氏法则所进行的一个粗略推算,做不得准。只有大约5%的产妇在在预产期当天生产。
临近预产期的日子,一家人每天都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谁也不知道小哼哼会在哪天突然降临。
彼时,国庆长假将至。若在放假期间生产,有点担心医院人手不足,万一出点什么差池就麻烦了。于是,我和夕同学每晚都隔着肚皮和小哼哼进行友好的磋商——
“臭哼哼,你28号粗来玩好不好啊?“
“吼啊!”
“妈妈也兹瓷吗?”
“当然啦!”
同时,我还和小哼哼进行了亲切的会谈——
“哼哼,你又在肚子里鼓包包玩啦?来,爸爸唱首歌给你听——‘大包整多两笼,大包整多两笼,大包整多两笼,唔怕滞~’”
此外,还就关心的问题进行了采访——
“哼哼,你到底是个男哼哼还是个女哼哼呢?”
”该给你买什么颜色的小衣服呢?”
然而,小哼哼一直很淡定,在肚子里悠哉游哉,并不着急着离开温暖的母体。过了预产期三天仍没有要发动的意思。这时国庆长假已经过半。
预产期已至,未能成功解锁。
10月4日,夕同学遵医嘱到医院做检查,次日开始住院。
10月5日,住院的第一天。办好了繁琐的入院手续,签了一堆制式的书面文件。之后是常规的胎监、B超等检查。
同仁医院南院的妇产科病房(虽然产妇通常身体较为虚弱,但分娩并非疾病,总觉得称为“病房”并不妥当),除了三间永远排不上号的单人间外,其余病房是不允许家属陪护的。每天的探视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17:00—18:30),且仅允许一位家属进入病房。探视规定之严苛,堪比探监,很是没有人情味。
妇产科区域有一道刷卡才能进入的玻璃安全门。门的内侧,有护士(或者护工)坐在一旁把守;门的外侧,是产妇们的家属。有的站在门前翘首张望;有的背着手来回踱步;有的枯坐在不锈钢长椅上,翘着二郎腿,手指在扶手上轻轻地敲打;有的扛来了行军床、充气床垫,带着被褥,拖着行李箱,搬来了成箱的矿泉水、一袋一袋的干粮和水果,做好了扎硬寨,打硬仗的准备。
产妇家属做好了扎硬寨,打硬仗的准备。
在非探视时间,要给产妇送饭、送生活用品时,能否短暂进入妇产科区域,全凭看守护士的心情。大多数时间,护士只打开一条门缝,让家属把东西递进去,由护工代为送达。在探视时间,倒是有通融的时候,有时允许两名家属先后进去探视,有时探视时间结束后也只是象征性地喊两嗓子赶赶人。倘若对护士美言几句,一般是能稍稍延长探视时间的。
三人间的病房,空间自然是不宽裕的。设施设备也略显简陋,与十一年前我的父亲在珠海住院时所在的病房相比都逊色不少。夕同学入院时是节假日,病房的浴室居然没有热水供应,据说是因为烧锅炉的工人休假了。只好从家里带来一个干净的水盆,接饮用的热开水,兑上凉水,用以擦拭身体。
待产包和女士便盆必须在医院负一层的小超市购买,价格不菲。待产包购买后不许打开,否则医院会不认账,要求家属再买一个新的。
病床的高度也不合理,坐在床边的时候,双脚无法踩到地面,是悬空的。这意味着下床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往下扽的动作。常人尚且觉得不便,产妇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是剖腹产后下地,这么一扥,恐怕会痛晕过去。后来只好去负一层的小超市买了一整箱矿泉水,放在床边,用作垫脚凳。
住院楼的四部电梯,其中两到三部永远处于检修状态。而楼梯的出口则大多被锁住了,只有一处需要迂回到门诊楼再绕回住院楼的楼梯可供通行。
尽管有这种种不便,好歹夕同学在第一天没怎么受罪。
这一天,我不关心什么屠呦呦、TPP,我只想着夕同学和臭哼哼。
10月6日,住院的第二天。医生使用普贝生催产,结果引发一起令人不快的风波。
根据医生轻描淡写的说辞,由于夕同学对普贝生过于敏感,宫缩得太厉害,导致婴儿缺氧,胎心一度不正常。医生不得不将药取出。取出后,宫缩较为规律。但胎儿因缺氧时扭动,胎心的位置发生偏移,胎儿的脸朝右,而非朝下,未必能顺产。
而按夕同学事后的描述,事情是这样的:早上本来安排8:00多开始用普贝生催产,但因为产妇多,医护人员少,分娩室空间不足,拖了许久,夕后来被安排在过道。塞了普贝生后,医生和助产士便置之不理。过了十来分钟,夕开始有了较强的宫缩、而且痛感越来越强烈。期间并没有医护人员前来查看。又过了好一阵子,夕再也难以强忍强直性宫缩引致的疼痛,且听到胎心监护仪的声音不对,好不容易才把路过的医生叫住。医生一看情况不对,这才马上紧急处置,取出普贝生,输液,输氧,给胎儿做B超。医生也讶异于夕同学对痛苦的忍受极限,喃喃道:“她怎么能承受得了这么强烈的痛感?”
之前对夕看也没看过一眼的助产士,这时候假惺惺地对医生说:“怎么回事?几分钟前我看的时候还好好的……”同样是这位助产士,后来在夕同学接她妈妈电话时为了宽慰老人家忍着痛楚挤出一点笑声的时候,阴阳怪气地说:“哟,这会儿还笑得出,看来今天是没戏了。”又在夕输液过程中血液回流到输液管,请求帮助时,对她大呼小喝。
可以想见,在听到夕描述这位助产士的言行举止时,尽管理智上知道,大概是因为人手不足和职业倦怠导致医护人员态度差劲,这位助产士很可能并无恶意,但我心里还是有一万匹脱缰的草泥马呼啸而过。
总之,同仁医院妇产科服务质量之差,态度之恶劣,远远超乎我的预料。这就是所谓三级甲等医院的妇产科。产妇和家属被一道冰冷的玻璃门阻隔着。里面的医护人员尽职与否,产妇状况如何,家属难以知晓。用夕的话说,简直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10月7日,住院的第三天。医生通知早上七点多开始挂催产素。夕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吃早餐。催产素必须持续挂上八个多小时。中途不便用餐,夕只能吃几个小蛋糕充饥。一直到下午四点半才结束输液。还好保温饭盒比较给力,中午盛好的饭菜,到这时仍是热的。
辛苦了,饭盒君。
10月8日,住院的第四天。由于担心像昨天那样,一大早就开始输液,导致没时间吃早餐,于是早上六点多就给夕送了早餐。结果这一天新入院的产妇剧增,医生忙不过来,一直拖到十点半才开始输液。用普贝生的那一天,由于护士在扎留置针时较为匆忙,针扎得有点偏,胶布也没粘好,要求护士重新处理一下,护士也不予理睬,夕的手浮肿刺痛,只好让护士先把留置针拔除。这次换了另一只手扎留置针。比较无语的是,输液架不稳固,一碰就掉,差点砸到了夕。输液管也短。夕只能保持着一个别扭的姿势,一动不动,确保输液能正常进行。由于胎心监护仪不够用,夕只能和另一位产妇共用一部。总之,条件比昨天还要恶劣。此外,夕所在的病房里,有一个身型肥硕的室友,晚上睡觉时鼾声如雷,夕已经几晚睡不着觉,加上折腾了几天,心焦气燥,到这时候已然头痛难忍。等输完液,做完胎监,已经是晚上七点多的光景。
夕这时精神已经濒临崩溃,吃晚饭的时候忍不住掉了眼泪,哽咽着说了一些丧气的话。和岳父岳母一同安抚了许久,陪着散了一会儿步,情绪才渐渐平复,头痛症状稍有缓解。当天晚上不得不打了一针安定剂(护士是直接在她手上的静脉注射,而不是在胳膊)。针还没推完,疲倦不堪的夕就已经睡着了。
10月9日,住院的第五天。上午九点半开始继续挂催产素。由于手上的静脉里有安定剂的残留,输液时疼痛难忍,只好又换了另一只手扎留置针。于是,五天内扎了三回留置针。昨晚睡了一觉,夕的情绪明显好了一些。听着歌输了八个多小时的液,做完胎监,已是傍晚六点十几分。趁探视时间还有最后十几分钟,岳母到病房的浴室里帮夕洗了个头,夕的精神又爽利了点。新的进展是:宫颈已经比较软了,然而宫颈管依旧有一半还没消失。主任医师说,再给两天时间自然发动,明后天(恰好是周六日)再没动静,周一就安排剖宫产了。
10月10日、11日,住院的第六、第七天。由于不用继续挂催产素,只需要做一些例行检查和术前准备,间或吸吸氧,夕的日子稍为好过一些。吃饭比较从容,有时可以出来外面坐一坐,聊聊天,散散步。我们之间的对话,逗比指数也恢复到正常水平。B超的结果显示:尽管已经快满42周了,但羊水的状况良好。胎儿估重六斤七两。胎心监测偶有偏高或偏低的情况,在吸氧后旋即恢复正常。比较苦逼的是,第三根留置针因为血液回流较为严重,只好又拔掉,准备扎第四支……
截至10月11日,预产期已过了十三天。虽然有假性宫缩,但期盼已久的自然发动并未出现。只好接受现实,做好剖宫产的准备。
这娃简直是个小哪吒。我要去苦学100%被空手接白刃的绝技了……
等待的过程漫长而煎熬。里面的产妇换了一批又一批,外面的家属走了一茬又来一茬。天南海北,口音各异。每隔一两天,原来熟悉的面孔就不见了。只有我们还在继续熬着。
除了送饭、跑腿,我每天在外面枯坐超过十小时,只能通过打电话、发微信了解里面的情况。夕的状况不太好时,难免焦虑不安。情况稳定时,就看看电子书,查查资料。岳父母在的时候,便陪他们聊聊天,聊祖辈父辈的经历,南北习俗的差异,听他们讲在毛时代的所见所闻,还有那些几乎未曾谋面的亲戚们的人生际遇。
尽管有诸多不便与不快,产科病房毕竟是一个喜讯频传的地方,有别于十一年前陪侍父亲时所在的癌症楼的压抑和绝望。在病房外已经等待了一周。在此期间已有二三十位产妇先于夕同学分娩。不时能看到初为人父者混杂喜悦和茫然的神情,还有老人家的喜逐颜开。然而也不乏泪水。曾见过产妇傍晚出来“放风”时伏在丈夫肩膀上痛哭流涕。据说情况和夕相近,用了普贝生,强忍了两天的疼痛,却未能成功分娩。也曾听过流产的少女在打电话向母亲倾诉时泣不成声。产科病房区域内外,每天都上演着着类似的故事,晴雨不定,悲喜交织,
10月12日,终于等到了迎接小哼哼诞生的这一天。我清晨五点多就醒了。岳母岳母醒得更早。囫囵吃了早餐,便赶往医院。在忐忑中等了一个多小时,护士开始招呼我进去。和医护人员一同推着内科的手术床,把夕送到手术室门口,我便被拒于门外。这时候是8:13。
9:00,和麻醉师在洽谈室签署了《麻醉知情同意书》。之后,我以为还需要签署一份《手术知情同意书》,可是一直没有下文。误以为是因为里面的手术台有限,正在轮候。只好继续等待。等到9:50左右,在手术室门口张望的岳父突然用手里的保温杯敲击家属等候室的玻璃窗,急切地招呼我和岳母过去——原来小哼哼已经被医生放在小车里推了出来,正在张开嘴巴哇哇大哭。
事就这样成了。
2015年10月12日,终于解锁成功。
这一幕出现得太突然,我一时激动得有点发懵。忍不住伸出手去轻轻触碰宝宝的小脸蛋。岳母问了一句:“是男孩还是女孩?”医生揭晓了谜底:“女孩”。
和医生一同将小哼哼推回产科病房的途中,我询问夕的状况如何,医生说:“没事,挺好的。你爱人真逗,小宝宝刚生出来时,她就说:’嘴巴这么大,这长得像谁啊?!’”我仔细看了小哼哼,这时依然张开嘴巴哇哇地哭,于是显得嘴巴有点大。到了产科护士站,小哼哼被推进去洗涤,称重,量身高,我则在略微懵懂的状态下填写签署了几份关于接种疫苗的文件。随后护士告诉我说:“宝宝7斤重,身长52公分”。想再仔细看一下小哼哼,然而她旋即被抱进了观察室,我则被撵了出来。于是回到手术室门口等候夕。据说剖宫产术后需观察两小时,我看了一下时间,一时半会儿应该还没能出来,于是给亲人、朋友和同部门的同事报了个喜,给我老妈打了个电话。手术室门口信号很差,只好稍稍走远几步。不料术后观察时间缩水,还没打完电话,就望见夕的手术床被推了出来,岳父母已迅速赶到床边。我匆忙结束了通话,冲到床边。夕的神情看上去疲惫不堪。我捋了捋她前额的刘海,她的嘴角动了动,试图浮现出一丝笑意,然而这笑意旋即被倦意所覆盖。于是和医护人员一同把手术床推回产科病房。把夕从手术床搬到病床上,输液,上镇痛泵,连接心脏监护仪。
小哼哼也被放在婴儿车上推进病房里了。仔细打量她的小脸蛋,和我与夕同学的画风相当一致。长得挺白净清秀,鼻子高高的,眉毛弯弯的,下巴尖尖的,人中和嘴唇的线条柔美秀气。微微睁眼时,黑溜溜的眼珠几乎充满了整个眼眶,还能看到明显的双眼皮,简直不像刚出生才两个小时的婴儿。她的嘴巴一张一翕,彷佛在急切地宣布自己是一个萌萌的小吃货。过了一小会儿,小哼哼开始把两只胖嘟嘟的小手伸到嘴边吮吸,说明她已具备了一定的行为支配能力,手、口动作相互协调已达到一定水平。
2015年10月12日,小哼哼终于降临人世。
当我凝视她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上始终带着情不自禁的微笑。夕同学在一旁轻声说了一句:“你前世的小情人终于出来啦!”
巧合的是,夕的病床编号是12号,做剖宫产的手术台编号也是12号,小哼哼出生的这天也恰好是10月12号,距预产期恰巧推迟了12天。12还是我上高中时的学号。
这是入院以来的第八天。
10月13日,住院的第九天,也就是夕剖腹产后的次日。最艰难的时刻是第一次下床。当我和一名护士一同搀扶着她试图站起来的时候,夕痛得撕心裂肺,又坐回了床上。整个楼道几乎都能听到她的惨叫声。所幸那位护士很和善耐心,不断地以她自己剖腹产后第一次下床的亲身体验来鼓励她,宽慰她。几经努力,夕终于借着我和护士的力艰难地站了起来,然后趴在我的身上,忍着剧痛,双脚几毫米几毫米地往前蹭,我则几毫米几毫米地往后退,就这样一点一点腾挪到洗手间。
是日,给小哼哼办理了医学出生证明。我在信息表的“婴儿姓名”一栏,一笔一画郑重其事地填上“元淇暄”三个字。
关于小哼哼的名字,我们曾商量过:如果是个男孩,就叫“元亨利”,取“元亨利贞”之意,将来等他长大了,就跟他讲解名字的含义:“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这个名字倒是浑然天成,连英文名,法文名都是现成的,就叫Henry。如果是个女孩,就叫“元淇暄”,“淇”字取自“瞻彼淇奥”。夕同学的家乡就在淇河边上,而我的第二故乡珠海亦有淇澳岛,两地南北相望。“淇”字暗示她的血脉纵贯南北。“暄”字则取自“负日之暄”。恰巧她出生的那一天,天清云淡,风日洒然,正是享受负暄之乐的好时节。将来要给小哼哼写一幅字——“瞻彼淇奥,负日之暄”——挂在她房间的墙上。
10月14日,住院的第十天。夕同学的恢复情况差强人意,上午下床时虽然还需要将病床摇到最大的倾斜角度,慢慢腾挪着才能勉强起身,但比起第一次下床时已经好了许多。然而,到了下午,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夕的乳腺发炎,低烧持续不退。我遵嘱回家将吸奶器清洗干净,匆忙送进病房。所幸将乳汁排空后,体温逐渐恢复正常,并无大碍。然而,乳腺的问题后来一直困扰着夕,为此连夜挂过两次急诊,打过几天吊针,外敷内服过不少药,还请过几次通乳师,至今仍未全然解决。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10月15日,住院的第十一天,剖宫产后的第三天。夕同学和小哼哼终于出院了。
这漫长而煎熬的十一天啊!总算是熬过来了。
如今,小哼哼已经出生50天,已经会甜甜地笑了。 抱着她,低头凝视她黑漆漆的眼睛,想起了卡门·G·史密斯的诗句:
“我们说她是我的底片,因为她高明度的皮肤。
她是光明也是通路,是我大脑皮层中的荣光。
女儿,你从哪里找到这些女神?
她的眼睛是暮光里聂鲁达的两汪黑色池溏。
……而在她的内部是我的胆色我的音质,还有我的无所顾忌。
(We said she was a negative image of me because of her lightness.
She's light and also passage, the glory in my cortex.
Daughter, where did you get all that goddess?
Her eyes are Neruda's two dark pools at twilight.
……Inside her, my grit and timbre, my reckless.)”
出生后一周。
出生后一周。
出生后一周。
出生后两周。
出生后一个月。
抱着你,就像抱着全世界一切美好的事物。
2015年10月5—15日用iMemo App速记于同仁医院南院。
由于iMemo有bug,文稿一直无法打开,直到12月初才恢复正常。
2015年12月4日晚在北京家中整理完毕。
2015年12月5日稍作修订。